田沁鑫:審美隨善而行 奇跡自然會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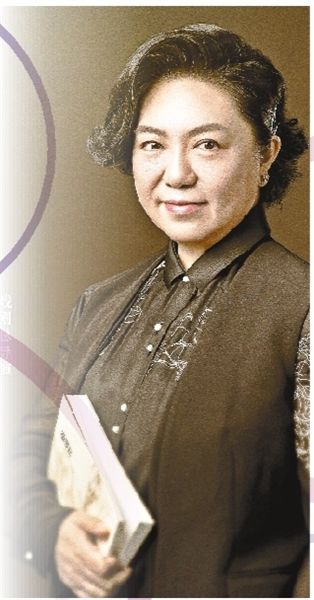



田沁鑫編導的《扶貧路上》在廣西試演成功


王曉溪 攝
從因悲傷而做戲,到國家話劇院分管藝術創作的副院長,短短兩年的時間,田沁鑫再度發力,蛻變成為為人民發聲、為時代抒懷的使命導演——國慶晚會《奮斗吧!中華兒女》的副總導演、“白玉蘭獎”最佳電視綜藝節目《故事里的中國》的戲劇總導演,全國現實題材及革命歷史題材舞臺藝術重點劇目民族歌劇《扶貧路上》的編劇、導演……她用自己一貫的中國美學、文人風骨講述著主旋律故事,也圓滿著自己用藝術“描繪眾生”的小小野心。
第一次真正參與電視節目疲憊至極
但狀態卻是高興的
2020年8月7日晚,第26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揭曉,《故事里的中國》摘得了其中備受關注的“最佳電視綜藝節目大獎”,就在此時,節目的第二季已經悄然開始錄制,而田沁鑫也一頭扎進懷柔影棚,開啟自己并不擅長的熬夜模式。戲劇+綜藝的原創表達,讓這檔國話和央視聯手打造的文化季播節目,從第一期“永不消逝的電波”就以爆款之勢橫空出世。
作為《故事里的中國》的“戲劇總導演”,田沁鑫是代表國家話劇院,帶著向經典致敬的“光榮使命”進入的,“第一季我們做了很多新中國70年來改編的故事,第二季則大部分是原創。新中國新時代真正感人的故事,文藝加工的素材少,難度大,創作中一直被人物原型感動著。”
雖然之前也做過不掛名的策劃,但這次卻是田沁鑫第一次真正參與電視節目的錄制,熬夜、晨昏顛倒是常事,疲憊至極,但狀態卻是高興的。“每一個都是新鮮的故事和人物,第二季舞臺上還會出現不同的地域環境,比如鐘南山這一期,舞臺上就會出現動車和天河機場,以及從武漢到北京的場景轉換,包括那段時間頻繁出現在新聞中的武漢金銀潭醫院,這些記憶中的場景都會用大屏和演員的表演來還原。”
回首第一季,田沁鑫毫不諱言:“每一集我都喜歡。但最難的是《橫空出世》那集,那一期是以錢學森為原型展現原子彈的誕生,為了呈現塔爆基地,我們第一次在主舞臺上換景,原來我們是希望把戲劇舞美做得簡潔些,但這次不得不換景真是一個課題,好難完成。經歷了這次,到后面的《青春萬歲》,那就是愉快地難著了,從教室到天安門廣場,展現青春的聚集,現在回想都不知道當時是如何完成的。”
“第二季《故事里的中國》中必定要展現抗疫故事,其中一集叫做《戰役中的青春》,我們專門邀請了北大援鄂醫療隊的90后,教演員們專業知識,包括如何快速穿脫防護服和搶救的流程,我很關心演員的專業度,甚至包括舞美設備,經過影視化拍攝要還原一些場景,每個細節的真實性和語言上的真實性就顯得格外重要。”
胡歌用表演詮釋了
“戲是妄語,我卻認真”的境界
作為國家話劇院分管藝術創作的業務副院長,時任院長周予援將《故事里的中國》以任務的形式交給田沁鑫時,她不僅沒有推辭,甚至還有些興奮,“借助電視媒介,我終于可以深入接觸這個世界了。但沒想到,真正一上手就又回到了一線,進入了一個干活的狀態,電視工作者非常辛苦,也只有年輕人能夠熬夜完成。”
今年國慶期間開播的第二季,田沁鑫覺得很多故事都非常精彩,“比如《十八洞村》,隸屬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但其實是云貴川聚集的地點,生活在這個地域,人說話方式會有些串,讓演員說這樣的話,我其實有點擔心,但王雷最終的呈現,我只能說我被演員震動到了。”
《故事里的中國》除了題材故事本身正能量的傳遞,明星演員也成為創意的看點。“胡歌是讓我尊敬的演員。其實在《永不消逝的電波》前,我們先是合作了國慶70周年的晚會《奮斗吧!中華兒女》。其中‘共和國之戀’的戲劇片段展現的是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以身許國,在飛機失事的一刻,用身體保護珍貴文件,最終讓公文包內的所有數據完好無損的故事。本來是一個朗誦式的片段,后來做成了戲劇化的演繹,其中演到他坐飛機遇顛簸,離地面還有400米時和警衛員一起抱住公文包的場景時,感動了觀看的每一個人。一個人品質的高尚,如果僅僅是表演,那只能是形似,人之偉大就體現在關鍵時刻的一瞬,能否丟去小我,成就一個偉大的靈魂。為了那個生死攸關的瞬間的表現,胡歌一次次在平地練習摔倒,他沒有偶像包袱,演員大都敏感,甚至有點神經質,但胡歌卻不,他很從容冷靜,總是以一種很安靜的狀態去接受導演的話。此外,他還是一個求真的演員,《永不消逝的電波》中,在演與妻子分開時的那段戲時,妻子問他能不能對孩子發誓,那時的他不可以撒謊,胡歌的表演是沒有回答,而是擁抱了妻子。胡歌提出這樣的處理后,我毫不猶豫答應了。一個演員能有這樣的思考,能用更好的方式來詮釋他與妻子的愛情,其實和他本人的坦誠有很大關系,他用表演詮釋了‘戲是妄語,我卻認真’的境界。”
每拍完一個新故事
都有種從虛空中落地的快感
每拍完一個新的故事,都讓田沁鑫有一種從虛空中落地的快感,“那是一種讓人忘掉疲勞的外在環境的刺激。”
《故事里的中國》第二季中,關曉彤出演的是一個真實的蒙古草原題材的故事,講述了一個孤兒養育28個孤兒的民族團結的傳奇。“拍攝時,有兩匹馬會上臺,還會尿在舞臺上,現場充滿了草原的真實味道。關曉彤是地道的北京姑娘,但為了接近人物,這次則要說蒙古族普通話,而關于這個民族的普通話,我們其實并沒有耳音,很難捕捉到語言關鍵詞的特點,但演員真的太棒了,關曉彤和曾黎非常快就進入了那個語言體系。”
田沁鑫還用導演特有的方式點評了給她印象深刻的幾位演員,“可以說《永不消逝的電波》是劉濤的話劇處女秀,她的爆發力非常好,原來我覺得她就是個很明媚的大姑娘,沒想到她的爆發力強,投入也很快。之前她曾經在軍隊里演過小品,舞臺形象非常好。吳謹言沒有偶像包袱,也不諂媚,通常的狀態是坐在角落里背詞,年紀小但很用功、敬業,即便拍攝到凌晨3點,她每次都能哭出來,還主動要求妝再化得樸素點。辛柏青在《鳳凰琴》里出演的校長操著一口河北話,倪大紅的‘座山雕’,雖然生活中還是那樣蔫蔫的,但鏡頭前控制力很強,還有郭濤的《平凡的世界》,《烈火中永生》里的劉燁和陳數,以及李乃文、涂松巖和閆妮,都讓我印象深刻,還有李光潔,真是越來越有型了。演員們對于這種60%影視化、40%戲劇化表演的分寸掌握真是非常精準。”
戲劇與電視結合
從創意到完成需要一個復雜的工序
在田沁鑫看來,如果沒有這次擔任《故事里的中國》戲劇總導演的經歷,她在國話是不可能有在這么短的時間做這么多現實主義題材作品的機會的,“每一集都是半個小時的‘大戲’,也給了我嘗試影視化拍攝的契機,欄目組的年輕人很敬業,要求也很嚴格,從劇本呈現到文化訪談,文字的完整度和采訪的邏輯性都很優秀。”
戲劇與影視結合,此前被認可的范本當屬英國國家劇院的戲劇電影,“我們一直在探究戲劇可以和影視結合的點在哪里?影視化拍攝的視角從哪里切入?我們都喜歡NT live(英國國家劇院的戲劇電影)用電影記錄舞臺的方式,采用的是戲劇的表演方式以及電影化的拍攝手法。而《故事里的中國》是在電視平臺播出,這樣的方式對我而言是全新的。內核是結結實實的戲劇故事,守正創新的意義在于要完成扎實的有邏輯的故事,要從表演上看到中國戲劇演員的水準和導演對結構的把握。戲劇本身有著嚴密的心理邏輯,需要短時間把一個故事編織出來,而與電視手段結合后,其實是同戲劇完全不同的創作方式,從創意到完成的結構比較復雜,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工程。工作的方式是,先要做一個故事,然后導演組需要找很多的資料,各種真實翔實的資料,之后再找專家論證,以確保專業用語萬無一失。編劇確立故事后導演組需要確立主場景,然后是作曲、找演員,燈服道效化全部到位后,先進行群眾演員的戲劇排練,主要演員進入后再進行圍讀,半個小時的呈現工序其實很多很多……”
田沁鑫認為,從第一季到第二季,難在很多人物是當代大家所熟知的,“比如鐘南山院士,大家都很熟悉,我們通過看書、看他的報告文學傳記,搜索到可以成為故事的元素;比如犧牲在扶貧一線的‘第一書記’黃文秀,我們也是從素材中找故事;包括雷鋒,除了苦難的童年,應該怎樣把雷鋒精神提煉出來,我們反復討論,向雷鋒同志學習的是什么?我們甚至還展現了他的前史,比如為了見他的老鄉毛主席,在金水橋等毛主席下班,結果沒有等到。還有在抗疫斗爭中擔當大任的90后,我們著重表現了他們在飛機上忐忑的內心,畢竟下了飛機就是戰場了,戲劇是可以說出心靈秘密的,援鄂醫療隊的隊員看后說很感動,說出了他們的心里話。”
作為導演,我一直敬畏我的職業
近日,田沁鑫剛剛在廣西完成了由她編劇、導演的民族歌劇《扶貧路上》的試演,對于黃文秀這個在花季年齡逝去的美好生命,田沁鑫的創作也可謂動了真氣。“都說主旋律題材不好做,做英雄人物有時會有超越故事和人物之外的一些遐想,把藝術審美和主旋律題材進行融合,我覺得其實是沒有障礙的。在做一部戲前,我不會過多去想是主旋律題材還是所謂的藝術題材,我想的是如何用藝術的形式來展現,不添枝加葉,正常就好。審美本身是隨善而行的,奇跡自然會發生,而不要去創造奇跡。民族歌劇本身就是一個新課題,沒有一個規律可以去尋找,需要我們自己去重新定義它。”
兩年間,劇組主創曾經八次赴廣西采風,第一次去百色時,田沁鑫和黃文秀擦肩而過,后來在她罹難第10天,田沁鑫到了她的出事地點,那時道路還沒有修復。“我當時就和這個姑娘有了一個感應,當時有一種很大的黃蝴蝶向我們飛來。廣西有一個傳說,死去的親人想念家人就會飛回來看看,村長說這是黃書記來看我們了。傳說是美麗的,我們也帶著這樣一份感動來為她和290萬奔跑在扶貧路上的‘第一書記’做這出戲。黃文秀的工作環境不是簡樸而是簡陋,非常詳細的三大本貧困戶調查顯示著她工作的細致。這個姑娘很會唱歌,長得也很好看,笑起來非常可愛,開朗愛笑,但就是這樣一個一眼看上去就會讓人喜歡的姑娘,到臨走都沒有休息,非常累,扶貧攻堅決勝之年,她卻沒有看到決勝時刻,就像脫貧路上的一枚鋪路石。我們就是想為她做一個符合中國審美的好故事。”
在田沁鑫看來,這不是大道理,她確實是懷著感恩的心來履行國家給予的一分殊榮和使命。“我希望自己的參與是對于民生和國家建設的一分凝聚。今年‘兩會’上唱國歌時,我突然鼻子發酸,這不是奧運奪金的那種感動,抗疫的艱難,國外勢力的壓力,我能感受到國家的那份艱辛,藝術創作是我的分內,沒有理由不做好。作為導演,我一直敬畏我的職業,職業給我帶來一份承認,藝術工作給我的是一份安定和安全。至于劇院的行政工作,我還是在學習階段。劇院今年會著力推青年導演,舞臺記錄電影的拍攝也在摸索中,時代是向前的,線下的劇場藝術也要迎接線上的到來。”(郭佳)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